今日要闻
富和穷,成了老班章村最典型的反差,2004年是这两种极端生活的分水岭。而茶叶,则是他们生活巨变的魔法师。树上的一片片叶子,套现成一张张人民币后,村民也一点点变得疯狂。
班章古树茶林,茶农们在清晨伴随着“嫩坝山”(哈尼语)上的第一缕阳光,上山采茶,这些古树茶生长在1700米至1900米的布朗山雨林中,最少都有百年以上历史,自古以来,老班章村民沿用传统古法人工养护古茶树,遵循民风手工采摘鲜叶。
“妈的,这鬼路,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好。”
三菱猎豹用15迈的速度,行驶在波浪式的山路上,车主杨文嘴里碎碎地抱怨着,右手则不断地在1档和2档之间来回拨弄。在这种山路上,2档以上的档位基本是弃用的。
汽车颠簸在路上,两边车轮走过的路面的最高落差会有50公分左右,车子经过时,我们就像坐在一个充分摇起来的摆锤上,车钥匙撞击车体发出的金属声从未停过。路的另一边,便是万丈山崖。
杨文的姐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她时不时地按下电动车窗,向窗外吐口水。
“妈的,嘴里都是沙子,吐都吐不完。”每吐一次口水,她就这样骂一句。车台上,一层黄色的灰尘像布一样铺开,在猎豹摇摆间,车内的空气都是乡土的味道。
从勐海县城到勐混镇是一条柏油路,从勐混到曼弄村是一条柏油混合拳头般大小的石头铺就的路。这样修路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汽车在山路上快速行驶。
到了曼弄,向右拐,便上了这条波浪式的山路。尽管这条路不限速,也见不到交警的影子,但从来没有司机会超速。
“开到20(迈)以上,人的屁股是基本上离开座位的。”杨文说。
越过这条长度为32公里的也许是中国最烂的山路,就到了也许是中国最富裕的村庄——老班章。这个因茶而富的村庄,现有127户人家,每户人家采茶的年收入均超过百万。从这个村庄出去的茶,也以老班章命名。
仅仅在10年前,把这个村庄称为中国最穷的村庄也不为过。那时,他们甚至要到别的村庄讨饭吃,才能保证一日三餐。
在通往老班章的公路上,一些广告商会把汽车广告写在四方形的木板上,就地取材,钉在公路两旁的大树上。其中一个悍马广告这样写道:遇山过山,遇水过水。
在别的省份,通往乡村的公路上,很难见到这样的广告。在内陆省份,我见过最多的广告是摩托车,还有彩电,最普遍的就是一些床垫广告。
汽车一路扬尘,就算仅仅相差5米的距离,也绝对看不清楚前车的尾号牌。扬起的灰尘,落在行人身上,已是一头灰白,就像刚在地上打了个滚。
32公里的路盘旋在6座大山上,经过4个小时的颠簸,一个依三角形的山坳而建的村庄——老班章出现了。
没人要的茶叶
朱琪上老班章村时,已经过了每年春茶最好的采摘期。她是勐海本地的茶商,在老班章茶最疯狂的2007年后进入茶业行当。
每年3月,都是最好的春茶采摘期。朱琪那时候压根不敢上来,“卖得太贵了,手上都不敢压货。”此次上山,是应客户要求,买了5公斤茶叶。今年老班章的古树茶最低每公斤可卖到6000元,一些单株的古树茶最高可卖到一公斤6万元。
朱琪觉得,这种疯狂类似于2007年。因此,对于她这种小本茶商而言,规避资本风险才是第一位的。“客户要,我就上来收点,客户不要,我就不往这个方向来。”
4月的老班章,只有老人还在留守,年轻人基本上都下县城过傣族新年了。在村里,我偶尔见到一年轻人,长方形的鳄鱼钱包紧插在屁股的右口袋里,牛仔裤配黑色的大头皮鞋,头上打着发蜡,闪闪亮。这种90年代初期在广东流行的打扮,被这位年轻人复制到了村里。
他也要去县城,出门前,父亲给了4000块钱。他单身的二姐,拿了6000元,至于那个负责家里财务的大姐,他也不知道到底拿了多少钱。“就去县城,玩两天,就回来。”
杨文的姐姐觉得,村庄富裕起来后,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多得太过分了”。“他们已经忘了穷日子是怎么过的了。”
朱琪第一次来到老班章村是2001年,那时她15岁,跟着姐夫上山为村民的房屋安装不锈钢。当时,这个村庄的房屋多数为木质结构。
村民的热情给朱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现在村民的冷漠给她的印象一样深刻。“那时候他们都是用口钢杯泡茶给我们喝。”朱琪说,“现在连一小杯都不舍得给你喝了,顶多给你一瓶矿泉水。”
不锈钢安装后,部分村民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便找朱琪的姐夫商量,是否可以用茶叶来抵部分不锈钢的货款。但她姐夫没有同意,理由是茶叶拿回去没人要。当时,一公斤茶叶最多只能卖到6块钱。
朱琪说,如果按照当时的市价,可以换回几百公斤的老班章茶叶回来。“早知道这样,我们换回来都发财了。”
在当时的老班章,用茶叶当报酬似乎是一种习惯。“太穷了,拿不出钱,又不好意思让人空手回去,就只能拿茶叶了。”村民杨文说。
朱琪的朋友张永德记得,在茶叶还不值钱的时候,老班章村有一个产妇要生了,下山请了一医生。为了感谢医生,这家男主人随手拿了一大袋老班章茶叶给他。医生下山走到半路时,看到路边有两个南瓜,便把整袋茶叶倒在路边,把两个南瓜装回了家。
杨政民那时还是老班章村村委会的副主任,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过高中的3个人之一。村委会设在新班章,离家10公里,每次回家,绕山路,要走两个小时。
当时的勐海茶厂在村委旁边设了一个茶叶收购点。老班章所有的茶叶都是通过这个收购点走向村外。茶农在跟收购点做买卖时,根本没有议价能力。“他们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杨政民说,那时候收茶叶,并没有分古树茶和小树茶,只按等级分为一二三。
如此,村民们摘茶动力没那么积极。他们对茶园也不怎么打理,任由茶树自生自灭,摘茶也只利用农闲时间,买多少算多少。“那时候,只要你愿意,你到任何一家茶园去摘茶叶都没人说你。”杨政民说,也没多少人愿摘,基本都是长在树上,看着茶叶一片一片老去。
搬出老班章
老班章的茶树在村民不理不睬的态度下逆势生长,这主要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老班章村位于海拔1700米的布朗山区。冰川纪,青藏高原挡住了寒流,让这里成为了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是长在这里。
茶树的繁荣并未给他们带去财富,这种环境反倒限制了别的农作物的生长,给村民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难。老班章村的土地很难种植别的物种,就连水田的产量也不高。这里5亩田的产量,还不如跟老班章相隔25公里的老曼娥村一亩水田的产量。
在这种环境下,吃不饱饭是村民的常态。于是,逃离老班章成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现在的卫东村,以及新班章村都是由老班章村民搬过去后建设的村庄。
当时,在没找到合适地方搬离之前,老班章的多数村民只得到周边稍稍偏远些的荒地上开荒,种点土豆,以及水稻等农作物填肚子。杨卫华的爷爷便是开荒者之一。
1965年,经多年经营,此地逐渐繁荣,农作物产量也比老班章高得多,杨卫华的爷爷便和其余60户人家商量,干脆搬了过去,不再回老班章。日后,这里为仍居住在老班章的很多村民解决了吃饭问题。
刚搬到这里时,村庄取名勐囡。一年后,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这里的村民为了表达他们誓死效忠毛主席的决心,便改名为卫东村。虽然与卫东村仅隔20公里,老班章村民得知文革时,这场运动已进入尾声。如今,这些村庄的村民家里仍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有些甚至还把瓷砖烧制的画像贴在墙上。看到这个场景,我仿佛穿越到了90年代中期。那时,这种画像在我生活的小县城——瑞昌非常流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挂在厅堂的正墙。“你们拜佛,我们拜毛主席,都是一样的道理。”当地一位村民说。
搬到卫东村头几年,在茶叶采摘季,杨卫东的爷爷还常带村民回老班章采茶。“那时刚搬到卫东村,自己在这边种的茶树还没长起来,空闲时就回老班章采茶自己喝,有多的再拿出去卖。”杨卫华说。
回去摘茶叶的还有新班章的村民,他们比卫东村更早建村。
他们在新村庄种的茶树长起来后,就很少回老班章了。倒是留在老班章的亲戚常去卫东村或新班章村串门,讨粮食吃。因为路途遥远,又无人愿意打理,搬出老班章村的人就把茶园送给了村集体。
当初,老班章的祖先搬到这块土地居住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辛苦争来的土地,子孙会因贫穷而逃离。今日老班章村所在地,是现老曼峨寨布朗族先民世居辖地。
1476年,老班章村的哈尼族先祖——爱伲人,从毗邻的格朗和山迁至此。他们为了能在这里长久生存下去,便向老曼娥寨布朗先人请求,把老班章村周边的山地、林木、田坝及漫山遍野且已有数百年树龄的大树茶一并给他们。慷慨的布朗先人如数答应。
后来,老班章爱伲人为了感谢布朗先人,每年岁末都会向老曼娥寨进贡谷种及牲畜,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90年代末才结束。“那时候人口少,田地又多,大家都够吃。”杨卫华说,后来,人丁兴旺,田地根本不够分,一些敢面对现实生活的人才开始寻求往外面居住,先后经历过两次人口迁出。
未迁出的李开华,依然记得去卫东村亲戚家讨粮食的情况。虽然老班章离卫东村只有20公里路程,但他每次都要走一天。“都是山路,很难见得到人。”李开华说,每次串门就带点茶叶,回来就可从亲戚家带一小袋大米。他基本上每两个月就要跑一趟卫东村。
搬到卫东村、新班章村“可以吃饱饭”的消息传到老班章后,留守村中的人非常羡慕,包括李开华在内的多数村民在断粮的情况下,都会跑到这两个村庄讨粮。以至于李开华他们都想搬离老班章。
最终,李开华还是放弃了。他觉得,先前搬过去的人早已站稳脚根,而自己过去却只能从头开始,“还不如守在老村里等机会。”
通往山外的路
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当村民们得知文革时,已是1974年,革命已近尾声。为了跟上潮流,他们在村里也搞起大批判,但形式却没有外面世界的那么激烈。他们把一个此前是地主的人拉出来,让他写了一封检讨书交给村委,然后就放回家了。“当时村里人以为这就很厉害了。”李开华说。
村庄的节奏比外面的世界总是慢了半拍。老班章村民也想让村里跟外面世界接轨,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可村里得到这个消息已是两年之后,这个村庄仍在继续文化大革命,依然批斗那些前地主。
直到有一天,老班章的村民才从来自卫东村的亲戚口中得知,原来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这才明白,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这一次,这些从来没有出过大山的老班章人,终于超过了中国的节奏。1981年,在村民的要求下,他们开始把茶园以及田地分到各户。杨政民说,那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小岗村。1978年,安徽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集体的时候,村民的积极性太低了,种的粮食又吃不饱,大家都觉得应该自己干自己的。”杨政民说。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才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建国5年后,布朗山乡政府成立,老班章归其管辖,但因山路遥远,政府人员除了送毛主席画像,基本不到村里。杨政民说,这倒给了老班章村民一个自治的机会。
幸好,他们不知道分田到户的危险。“如果知道这样做要坐牢,谁愿意冒这个险啊,就算饿死,也得跟着吃大锅饭。”杨政民说。
分田到户后,老班章村民种农活的积极性明显提高。1980年代末,这个村庄的民众终于脱离饥饿。如果天公作美,他们种的粮食刚好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
但茶树上的叶子依然不值钱。当时的中国,可口可乐才是一种让城市人着迷的饮品。10年前,中美建交3个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一批可口可乐产品从香港经广州运到了北京。
为了庆祝粮食丰收,他们在老班章村的空地上跳了一整夜的哈伲族舞。但他们的命运,仍像在茶树上随风飘动的叶子,不可掌控。“那时候真不想别的,能吃饱饭就好了。”杨政民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结束了爱伲人世代狞猎的日子。“那时候田地很远,我去趟我家的田要走13公里,要走3个小时才到,一般男子走路快的话要两个半小时才到田地。当时我们种田的时候,鸡一叫就爬起来,天亮就到田里,那时候真辛苦。”
解决温饱后,老班章村民开始不满足黑暗的生活,寻求光明。1992年,老班章村倡导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原始森林中的羊肠小道,将几百根水泥电杆抬上布朗山,终结了世代靠火塘和松脂照明的黑暗。
“要致富,先修路。”“养两个娃,不如养一头猪。”此后,这种白底黑字的宣传标语,在中国乡村的墙上随处可见。
10年后,有了光明的老班章村民开始谋求打通跟外面世界联通的道路。此时,杨政民已是老班章村的副书记。“我们村也要改革开放。”但显然,老班章人执行了标语的第一条,抛弃了第二条。在这个村庄,超生成了常态。
4月15日,在下山的路上,杨文指着波浪式的山路,说“这些都是我们当年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他觉得,现在的路已经算得上历史上最好的了。尽管依然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当时,路修到一半,挖到了石头山,用锄头已经很难挖下去了,村民们垂头丧气。杨政民带着两个村民找到县政府。此时,他们正赶上了政府鼓励在乡村修建公路。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准备修建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公路。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中国在乡村修建的公路里程的总和。
勐海县政府接着老班章村民挖不动的路继续修下去,让这个村庄结束了与世隔绝的日子,也让外地人和老班章人重新认识了茶树上的那些叶子。
“突然发现,树上长的哪是叶子啊,都是钱。”杨政民说。
长钱的茶树
村里修通公路的头一年,在收购站上班的白新文(音)找到杨政民,希望他能单独做点茶叶出来。“只要做出品质,他给我14块钱一公斤。”杨政民说,他乐得不行,当时的茶叶送到收购站每公斤最贵只能卖6元。
白新文要了10公斤,但杨政民为了茶叶的质量,只做了5公斤。这个茶叶作为样品带到了广东。当时杨政民拿到了70块钱,这对于年收入不足一千块钱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广东老板喝完老班章的茶后,大喜,便再向白新义要茶。随后,白新义以每公斤20块钱的价格向杨政民要了15公斤茶叶。2003年,已从村委副书记改任副主任的杨政民辞掉工作,专心为白新文做茶。
2004年,当杨卫华到老班章收购茶叶时,价格每公斤已涨到40元。这年开始,老班章村里开始陆续出现陌生人。“那些广东商人自己到村里来收购了。”杨政民说,村民们意识到茶叶没有那么廉价后,不再主动把茶叶送往收购点,而是留在家里,等待客商上门来收。
收购站的人意识到危机,也开始主动上门服务,跟广东商人竞价。此时的村民基本没有市场意识,一般都是客商出多少钱他们就认多少钱。有一次,一客商到杨文家里收茶叶,愿意以每公斤60元的价格收购。杨文听后,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齿。就在20分钟前,他把茶叶以每公斤40元都给了收购站。当时他还觉得走了好运,一转身,却没想,收入少了好几百块钱。
80,120,150,180,200。当年底,老班章的茶叶以这样的速度涨到了200元一公斤。且那时候,还没有大树茶和小树茶之分。
上山的外来人越来越多,村里人也开始下山消费。他们买回来的多数是手机,虽然那时村里还没有信号,但都喜欢把手机别在腰上。村民们对另外一种商品——保险柜的需求也很大,因为去县城存钱不方便,村民多数把钱放在家里。
在信用社上班的杨春平做了一个统计,老班章村一年的流动资金有一个亿。于是,他开始游说村民把钱存到他所在的信用社。
一开始,没有村民理他。“他们都觉得把钱放银行里不安全,他们还是习惯了那种原来的生活,什么都用现金。”杨春平说。
慢慢地,杨春平的一些亲戚答应可以试试。当亲戚把这些钱拿到信用社时,杨春平闻到一股霉味,摸上去粘粘的,放到数钞机上,这些钱无法通过。他只得让亲戚拿着吹风机,把钱吹干再存。
后来,再去存钱的人都知道,在家把钱晒干了再去县城。2013年底,农村信用社在老班章开了第一个村级银行。仅仅4个月时间,银行的存款额就达到了四千多万。
随着时间的流转,祖先留下来的茶树成了他们现在的财富。老班章人开始善待茶树,每年都会给茶园松两次土,除草、剪枝更是经常。茶叶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此时,新班章的人开始回到老班章,向村委会负责人索要之前送给村里的茶园。“有利益了嘛,他们当然就想要回去了。”杨政民说。
但老班章村民没有人愿意让出分到手的茶园。“隔了那么多年,要不是我们每年去除草,茶树早死了,现在可以卖钱了,他们就想到茶园了,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老班章一村民说。
几个村庄的村民都沾亲带故,他们也不好意思把事情闹得太僵,几次温和的讨要无果后,新班章人只得放弃。卫东村在后面见机行事,见新班章人维权无果,也不好意思向老班章村委开口。如今,一些村民仍在私下说,老班章人卖的是他们的茶叶,花的是他们的钱。说这话时,村民脸上带着羡慕。
200、300、400、600、1200……老班章茶一路上涨,疯狂到了2007年。唐海滨是一家茶厂的副总经理,他记得,当时山上的村民还只习惯用现金交易,他有次上山,带了3000万现金,装了几个蛇皮袋。
这些钱的一部分最终又通过那条路,回流到县城。城里人对老班章村有诸多抱怨,他们觉得老班章人把城里物价抬上去了。“他们进家电城,就跟进了菜市场一样,什么都不讲价,拉一车就回了。”
老班章村民也不知道茶叶到底值多少钱,他们只知道,他们睡一觉起来,价格又涨了。他们觉得不管喊多少价,都会有人要。“那一年真是疯了,外地来收茶的人见茶就要,不仅是老班章,别的普洱茶也是翻倍地涨价。”杨卫华说。
在这样的情势下,村民们也学会了随口喊价。有次,北京来的一个茶商向杨政民买茶,杨要1200元一公斤,但茶商只愿出1000元。交易失败,北京茶商走后不久,杨政民转身又遇一茶商,他喊1400元一公斤,茶商头也不回,从随身带的袋子里拿出十几叠钱,数给了他。
杨政民拿着钱,还没回过神,茶商就走了。他觉得跟做梦一样,甚至怀疑“那人到底是不是傻子”。
部分村民在利益面前开始变得不诚实。在老班章村,我碰到一位东莞茶商,他只准备在山上看看,不买茶叶。2007年,这位茶商在当地收了7户村民的纯料茶叶,回到东莞后却发现,只有两家是纯的,其余5家掺杂了别的次品毛料。这一年,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
不仅本村人,外村人也瞄准了老班章。一位外村人趁着夜色,通过山道,把两袋台树茶拖到老班章,第二天一早,以每公斤12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茶商。当时,这种台树茶最多值200元一公斤。
这种事情终被发现,村民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来保护。他们便商量,每两户一天轮流在进村的唯一一个路口把守,不允许任何人带茶叶进村。另外,本村村民也不得作假,一经发现,5年内的茶叶收入要充公。
就在老班章村民着急“钱怎么花”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引爆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这场危机完全失控。包括老班章在内的普洱茶,应声下跌。普通普洱茶跌回十几块钱一公斤,老班章则跌回2005年的价格——400元一公斤。
很多还未来得及把手中的茶叶出手的茶商在这波投资中倾家荡产。黄宏宽在勐海经营一个茶厂,他1000万买进来的茶叶,最后100万就转给了别人。他最终还是扛了下来,“扛不下来的,就跳楼了,勐海就有好几个。”
老班章村民的情绪也不太稳定,他们担心,“以后谁还会上山买我们的茶叶?”村民减少了去勐海县城的次数,“把钱存着过日子。”
当年11月,国务院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意在提振中国经济。此时,一家茶厂进驻老班章,建立茶叶基地,愿意跟村民建立长期合作。
中国经济在“兴奋剂”中一路高企,老班章的价格在这种趋势下,逐渐回暖。杨政民和许多村民一样,觉得有救了,纷纷与这家茶厂签订了合作合同。“不用愁了,鲜叶摘下来就卖给他们。”杨政民说。
尽管老班章村民很努力地采摘茶叶,尽量可能不抛弃任何一片可以用水来泡的叶子,但老班章茶叶的产量跟市场销售的数量永远不成正比。一位知情者说,老班章每年的产量为20吨左右,但在市场上销售的远远超过了100万吨。
这致很多人真假颠倒。杨卫华说,前年,一位上海商人向他要10公斤老班章,他特意去了村里一趟,给上海商人寄了过去。却没想,上海商人喝完后,给他回电话说,“兄弟,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以前喝过的老班章不是这个味。”
杨卫华把钱退给商人,让他把茶叶寄回来,挂电话后,他再也不联系这个商人了。“喝了一辈子假茶,喝到真的,就以为是假的了。”
忧伤的年轻人
在古树茶价格上扬之时,杨政民庆幸自己在2000年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那年勐海县政府决定,为了提高茶叶的产量,通过行政命令让茶农对茶树进行低改。“就是把大茶树砍掉,让它重新长枝发牙,这样茶叶的产量就会多出很多。”杨政民这样解释低改。
为了鼓励茶农积极性,县茶叶办的人允诺村民,只要参加低改,每家可得一袋化肥。茶叶办的人雇了十多辆摩托车,把化肥送到老班章,杨政民坚决不同意,村民也没一人愿参加低改。茶叶办的人气得连化肥都不要,转身就下山了。“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随便砍。”
在老班章人拒绝低改时,附近几个村庄的人正在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老曼娥村就是其中之一。“老班章的古茶树都是我们的先人留给他们的,我们要是那时候不砍,我们的茶叶肯定比他们卖得贵。”老曼娥村民玉光先说。
“这个政策,在只讲茶叶产量的时候,是很正确的。”回过头看当时的低改,勐海县茶叶研究所一工作人员说。“老班章当时之所以没砍,就是因为他们太懒了,茶叶不值钱,他们觉得劳动付出不值得。”
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没想,这种懒为老班章日后积下了巨额的财富。在这种财富还没有套现为人民币之前,老班章的女孩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她们通过村庄那条修好不久的泥巴路,背着行李,奔赴东莞打工。她们再也不甘心复制长辈们的生活——守在村庄,然后等到待嫁之时找个村里的适龄男青年结婚。在通往山外的路修通之前,老班章村的男男女女基本都是村里通婚。“外村的女孩子不愿意嫁进来,嫌太穷了,村里的女孩子又出不去。”杨政民说。
小诺(应采访者要求用化名)是老班章村外出打工最早的一批女孩子之一。她坦承,外出打工就是寻找离开村庄的机会。人潮中,她期望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在工厂里,她认识了一个湖南男孩,嫁了过去。那时,小诺心里窃喜,终于可以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至少可以比村里好。”在随后的几年里,小诺也未带着老公回老班章。那几年里,村里外出打工的女孩基本没有再回到村里。
村里的男孩则遵从父辈继家守业的传统,只得在村中从少年熬成白头。大量的女孩外出,导致村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因此村中至少有10年没有办过结婚喜事,直接导致村小学招不到生源而关闭。
这一切问题都在茶树上的叶子套现后迎刃而解。2009年初,老班章茶叶价格开始第二轮疯狂,回到两年前的水平。随后,从来没带老公回过老班章的小诺,带着老公回来了。她发现,只有回到老班章,才可以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凭着家族关系,小诺和老公在村里开了一家餐馆——只有4张木桌子。如今,这个村庄总共有了4家餐馆。顾客主要来自于村民。杨政民说,村民富起来后,很多人图方便,就直接叫餐馆送餐。
现在年轻的女孩,没人再像小诺一样,去外面改变自己了。她们只想在村里找个好对象。“嫁到外面去,嫁人家太穷,没条件比村里好的,她们不愿嫁,比村里条件好的,又没人愿娶她们。”一村民说。
有条件后,村里的男人不再愿意娶本村女人,他们大多以娶外村的女人为荣。“现在大家都比着,觉得把外面的女人接进村了,就是有面子。”杨政民说,如此,导致村里开始出现大龄剩女。
10年无喜事后,如今迎来了井喷期。杨政民说,最近几年,他每个月都要喝一次喜酒。当年,村里两个30岁还娶不到老婆的人,在他们40岁之时,各自把外村的姑娘接进了家。“这几年结婚的,30岁上下年纪的人多一些。”
村民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住上楼房。2009年,它村成了一个大的建筑工地。政府为了体现老班章的富裕,特意为老班章的新建设规划了一番。村民们终究觉得他们的效率太低,等不及,各自建房。“规划还没下来,就有人开始建了,有一家建了,后面的人都跟着建了。”杨政民说。
如今,村里的别墅,越野汽车,城里的商品房,成了老班章每户人家的标配。“都是一次性汇钱买的,没有人会去贷款。”
村里的年轻人更多喜欢追求身体上的刺激。一位常到老班章做生意的茶商说,有一次,村里一个年轻人为招待朋友,把他们请到县城一家宾馆,然后端出一盘小麻。
2007年后,布朗山派出所每年都要到老班章为年轻的村民做一次尿检。第一次,查出了5位青年跟毒品有染,年龄均在16岁左右。老班章一村民把这视为父母对孩子太宠爱了。他甚至觉得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多得太过分了。
您可能敢兴趣
声明: 凡注明为其他媒体来源的信息,均为转载自其他媒体,转载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也不代表本网对其真实性负责。如系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您若对该稿件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质疑,请即联系,本网将迅速给您回应并做处理。邮箱:mail@chazhishi.com
为您推荐

红茶控看过来!红茶种类那么多,爱喝红茶却不懂吗?
2021-06-14 15:36:53

日本人寿命全球最长 WHO:与日本抹茶功效有关
2021-06-12 15:16:44

为茶业注入新生命 他带动疯阿里山高山茶
2021-06-12 15:09:29

【图】茶叶制茶方法工艺流程图如何?
2021-06-12 13:56:15

茶叶品种分类好简单,红茶等级、产地、茶款一定要会看
2021-06-11 09:22:18

台湾蜜香红茶|台湾蜜香红茶功效与作用
2021-06-11 00:39:46

台湾日月潭红茶制茶6步骤方法
2021-06-10 22:41:53

熟成红茶好喝的秘密?专家带你从原料端看行销手法!
2021-06-10 13:19:41

世界茶种类大全,6款常见下午茶的味道特徵和风味特点
2021-06-09 18:23:55

红茶也有分等级?认识世界知名茶种
2021-06-09 17:09:59

被过度吹捧?茶叶专家解释为何大吉岭茶是红茶的正统
2021-06-09 15:55:52

台湾高山谷芳有机茶园 品一口土地的芳香 有机茶
2021-06-09 15:37:28

一杯有机好红茶的制茶过程成长史
2021-06-08 22:55:40

日月潭红茶赛「一条龙」较劲 採茶到焙茶比功夫
2021-06-08 17:16:19

传统全校采茶体验大悟、撒哈拉小软萌有礼
2021-06-08 16:57:07

中国博大精深汉学中医底蕴深厚 帝王级茶膏「龙裕泰」
2021-06-08 09:29:02

“一饼茶一辆宝马” 高档茶叶在中国作为一种送礼手段
2021-06-08 09:24:05

全台乾旱 春茶採收量锐减茶农苦哈哈
2021-06-07 23:48:49

绿茶、乌龙茶和红茶都生长在同一棵茶树上?专家解惑
2021-06-05 16:32:31

英德英红华侨茶场英红九号红茶品种和英红九号分级
2021-06-02 15:48:31

印度大吉岭产区红茶分级
2021-06-01 17:1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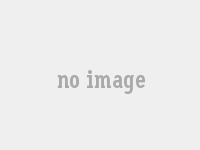
印度大吉岭红茶产区海拔和著名茶园风味特点
2021-06-01 15:52:20

阿里山高山茶去年底雨水少不发新芽 茶产量少3成
2021-06-01 14:41:06

嘉县阿里山高山茶春季优良茶竞赛 成绩公布
2021-06-01 14:28:35

正视气候变迁 别让肯亚红茶的美味成为记忆
2021-05-29 15:26:19

三芝茶旅 背起茶篓跟著返乡「中年」採茶趣
2021-05-27 20:06:29

老茶园变身亮点茶庄 林玉萍如何打造「茶服务业」?
2021-05-27 19:51:18

歌手林语菲老家1.4万坪茶园缺水欠收 又碰疫情打击短收近千万
2021-05-27 19:43:58

梨山茶农中年转行 不眠不休学做茶盼更精进茶艺
2021-05-27 19:27:07

阿里山高山春茶评鑑 上意茶业夺双奖
2021-05-27 19:25:18
今日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