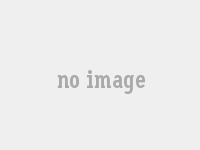用遥远一词,是有多层含义的。首先是指地理概念上的,要到娜波迪拉祜山寨,真的很远,这里属糯福乡,离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澜沧县城有100多公里,离云南省省会昆明近1000公里,距离北京5000公里左右那就更远了,相当于万里长征,过了阿里边防检查站再沿着中缅边界线中方一侧,还得驱车走上一个多小时,过了南段村再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10多公里才会到;其次是指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当1949年我国大部地区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时,这里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社会发展形态离我们很远;第三是指思想意识上由社会发展形态滞后带来的物质生产、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更大,离农业文明有一段很长的距离,离工业文明距离更遥远,离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第三浪潮更是遥遥不可企及。
当我来到紧靠中缅边界上的这个拉祜山寨时,不仅仅感到遥远,而且充满了一种神秘……
最后的茅草屋
到娜波迪我看到了已经快要消失即将变为一种历史遗迹的最后的茅草屋。
娜波迪30余户拉祜人家的住房除简易公路边有一间盖有石棉瓦外,其余全是茅草屋。这种茅草屋与我想象中的不同,它不完全是双斜面盖顶的那种汉族式结构,而是双斜面盖顶和一种少见的蘑菇式相结合的结构,当地人亦称为“鸡罩笼”或“鸡窝房”。远远看去这些蘑菇式的茅草屋沿着山坡错错落落排开,在周围竹林和灌木的映衬下,像一朵朵雨后林中破土而出的褐色蘑菇,别有一番风景;再让已经偏西的和煦的阳光一照,淡紫色的炊烟从茅草屋的蘑菇顶上轻轻飘逸出来,呈现出一种原始部落的旷古和神秘。

我在村武装干事的带领下慢慢走近这片蘑菇房,只见一幢幢蘑菇房分别建盖在几棵树桩搭建的简陋的掌搂上。通向蘑菇房的极其简易的楼梯是用整棵木头砍成一个个台阶斜靠在掌搂中间,有的蘑菇房开一个半人高的洞,人可以弯腰出来到同样是木桩搭建的“阳台”上。
一间蘑菇房前,一个拉祜族妇女正在给一个全身赤裸的小男孩用从林中引来的冷水洗澡,光屁股的男孩显得很可爱,我端起相机正准备拍照,拉祜族妇女见状机警地抱起小男孩躲进了蘑菇房,我多次试图接近进行拍照都遭到拒绝,我知道这不是肖像权的问题,肯定背后有什么原因,后来听说他们是害怕把灵魂也摄走了。
这就是一个边远的民族面对现代文明下意识流露出来的一种局促、一种惶然、一种不知所措和难以理解。
拉祜神鼓
在娜波迪我们终于看到了拉祜神鼓(拉祜语为“节谷弄”,“弄”是大的意思,“节谷”是鼓的意思),这是在拉祜族地区至今保留的唯一一面神鼓。神鼓平时存放在山寨的佛房里,不得随意敲响,更不能随便移动,只有每年春节的特殊日子,才能将神鼓拉出佛房,但必须抬到寨子中的寨神柱前。村上的干部看到我们心存敬意远道而来,特意为我们打开佛房,并请来了鼓手。
佛房仍然是一间茅草屋,虽然简陋但不乏神圣之意,进到充满宗教神秘气氛的佛房,我们看到仰慕已久的神鼓,神鼓长约1.5米,鼓面直径1.1米,是用整棵大树雕琢而成的;神鼓朝外的一面用公牛皮蒙制,朝里的一面用母牛皮蒙制,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神鼓用芒果树精心雕琢而成,鼓身雕刻有植物和动物的各种图案,象征着幸福、吉祥、丰收、快乐。拉祜鼓手用生硬的汉话告诉我,这些图案叙述着拉祜族的繁衍、迁徙、兴衰和发展的历史,有许多传说和故事,但他找不到相应的汉话来翻译。
在经过一番虔诚的上香和祷告之后, 拉祜鼓手破例为我们表演了敲神鼓。他时而舒缓、时而激扬、时而双臂轻展、时而舞步踢踏,击鼓动作极富变化,有时前后抡击、有时左右敲打、有时双手交叉后击、忽而又两捶翻转数点激下,鼓声就尤如阵阵春雷滚过。听见鼓声响,来了几个拉祜族村民,其中的一位年轻妇女很大方地跳起了木鼓舞,舞姿柔美而舒展,这倒有点让人感到意外,它一改边远民族的局促和羞涩,流露出的是拉祜民族骨子里对音乐对舞蹈对艺术的与生俱来的潜质和追求。
绿色环绕的拉祜山寨
离开娜波迪时已是下午6点多,赶回到阿里村的老迈寨太阳已快落山了。这是我在去时看好的一个拍摄点,一个很美的拉祜山寨,房屋排列有序,周围绿色绕。山里的夜色来得快,一停下车,我抓紧时间架起三角架拍摄,慢速、小光圈加爆光补偿,终于拍下了一张绿色环绕的拉祜山寨的照片。
傍晚的拉祜山寨真的很美,炊烟袅袅升起又被风淡淡吹散开去,似有似无,给山寨周围的绿色抹上了一层白雾。整个寨子此时显得很寂静,很长时间了都没一个人走动,只有一条狗懒洋洋地在寨中空地上溜达了一会又消失了。糯福林业站的同志告诉我,到了春节时可热闹了,到深圳、昆明、思茅等地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几天几夜跳啊唱啊,吸引得附近村子的年轻人,还有阿里边防站的军人都来凑热闹。这种介绍和眼前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看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不可避免的“中空现象”。
这张绿色环绕而又寂寥的拉祜山寨的照片让我想到了许多许多东西,也让我思索了很久很久。